
Francisco 教授是一位来自南非的学者,毕业于南非开普敦大学,获免疫学博士学位。他于2016年受邀来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并且成为极少数获得“中国绿卡”的外籍专家。2018年是Francisco来到中山医科大学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在他眼中,中国是怎样的呢?对于中非合作,他有什么独到见解?以下内容根据广外非洲研究院采访稿整理,以第一人称口述。
与中大结缘
“在开普敦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认识了来自中山医科大学的李兵(音译)教授。当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一起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说,我们非常欣赏对方。
毕业后,我准备申请去哈佛大学工作。我同时想起了李兵教授,于是也一并给中大发了邮件。哈佛回复认为我还不能达到博士后的录取资格,只可以去做研究助理。但是中大的回复非常热情,表示对我很感兴趣。
邮件中,中大甚至向我详细介绍了研究院的愿景、中国的发展、广州的美食、有多少外国人等等,一封邮件就包含了这么多信息,让我觉得中国人既开放又实诚。事实上,非洲人对中国还是存在一定的误解,觉得中国并不是个做研究的地方。非洲的学者还是更喜欢欧美的大学,像美国的哈佛、斯坦福。在大家眼里,中国还在遵循西方的脚步,并没有自己的研究。所以当你跟朋友们谈到去中国,会有很多人质疑,也给不出什么建议。”
“我问了许多问题。医疗保险怎么样?怎么获得保险?不喜欢这里的社会生活怎么办?我说我是个有家的人,我有妻儿。他们说别担心,你可以带他们过来,这里有许多外国人的孩子在上学,所以不是问题。于是我决定来这里。”
努力取得比在哈佛工作的同事更高的成就
在中国做科研,Francisco每天都充满惊喜。
“来到以后发现,这里的科研条件非常不错,比我很多朋友们的还好。即使我去了美国,我估计都达不到现在的成就。如果问我,是什么让我表现得更好?我想是勤奋工作的中国人民。是的,我必须承认非洲人有时候是很懒的。我是个努力的幸运儿,三年就完成了博士学位。在非洲或者美国或其他国家人们通常用四五年才能完成。”
“但是在这里,你能看到大多数人,我们的学生,他们非常非常地勤奋。有这样的学生在身边,相比那些只会说抱歉的人,更能推动你前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可以说是安全感。广州比我知道的城市都有安全感。至少在这里,你可以走路的时候打电话,但是在非洲这样就很危险。在这里我加班到11点甚至半夜,一个人走回家我都不害怕。”
“我在这里负责带学生,做研究,没有教学任务。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同时,我的妻儿在中国呆得非常开心,我也就更开心了。”
眼中的中国学者
Francisco认为,中国这边的研究设施达到国际水平。但是,他眼中的中国学者是羞涩而被动的。
“中国学者,(我的经验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的问题就是太害羞了,不够主动积极。例如,我在这边去联络一个教授,会耗时很久。在国外,人们今天见面,很快就能成为朋友。我们开始讨论自己的生活、分享当天的一切,但是在中国就不能这么做。我不能今天约了见面马上就能谈事情,更不用说是想要合作、做决定。在这里我们必须互相了解成为朋友。然后才能合作,耗费太多时间了。
比如说上周,我们部门组织了一场座谈会。我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澳洲的朋友。澳洲的朋友带来了当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论文,自己在那的项目。非洲朋友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的会议只持续了三天,但是我跟那位澳洲朋友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因为讨论了很多。但是跟中国人就没怎么交流。来自中国上海、北京、湖南和广西的学者,尽管我们交换了名片并且聊了几句,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好。可以这样说,当中国人还在准备怎么开始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已经完成了。这个问题会阻碍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接轨。”
“我不认为是语言的问题。他们英语说得挺好的。我们可以理解双方的意思,哪怕他英语不好。但这是在中国,英语不那么好很正常。我们也不能指望谁都能像我们或者英美的人英语说得那么好。其他地方的人比如法国人,虽然也不是英语国家,但是交流很积极。在这里(中国)呢,我们首先碰面,成为朋友,然后再谈关键的事情。我们得先用一个茶歇的时间寒暄,然后才进入主题。”
南非的公共医疗状况
南非是非洲地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南非,他们的公共医疗状况是怎样的呢?
“我离开开普敦已经很久了。南非有非洲最好的医疗系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做得还是不好。我们在主要的疾病像肺结核、艾滋病上有很大问题。比如说开普敦,有最多的肺结核患者。但我们基本没有瘟疫,如果有,那是因为与莫桑比克接壤。这是我们会有一点瘟疫的唯一可能。跟中部非洲不一样。我们的问题是艾滋病。
“现在南非和其他几个非洲国家也有非传染病的困扰,像心血管疾病。人们面临很多挑战,人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没有什么好吃的,却得了糖尿病。我们也有大量癌症案例。我认为除非人们改变文化习惯,现在他们太追随西方的生活方式了,这也是惩罚。垃圾食品的高油脂可能是首要原因。”
关于西药和传统医药
非洲的传统医药有悠久的历史。西方殖民统治时期,西方的医药系统全面进入非洲。对于传统医药和西药,非洲人民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我们很喜欢传统医药,不幸的是它还没有规制化。在中国,医院里可以看到人们排队买传统药品。医院虽然是现代的,但还是有传统医药。在非洲,我们也喜欢传统医药,但不幸的是,我们被西药、现代医药影响了。
我觉得问题出在我们科学家身上。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还不够。人们什么时候、如何获取传统医药是个问题。你去找你祖父,他可以给你一些药来治疟疾。问题是你祖父不知道剂量是多少,应该给你几升,给多少杯,不能量化。
当出现问题,人们就跑去找西医。作为一个当地医生,我们还必须长时间学习西医,才能取得资格证。我们没有传统医药制剂,即使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一些植物是能治疗疾病的,但我们没有量化的标准。这个非常糟糕。”
中国的传统医药在南非的应用前景
中国的传统医药,一定程度上和非洲传统医药是相通的。那么,传统的中医药,在南非的应用前景会如何呢?
“在南非,西医药的制度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对传统医药很感兴趣。我一个朋友来中国就是想看看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他打算研究传统医药。所以我确定这方面合作是可以有的,是我们需要的。在非洲,很多植物是可以治病的。但是量化的标准很重要,相信我,非洲人也需要传统医药。”
“但是,迄今为止,非洲有许多来自中国的骗子医生。影响非常糟糕,破坏了我们想要引进中医药的努力。我认为不要总想着让中药打进非洲市场,更要帮助非洲发展自己的医药制造,特别是非洲传统医药。从教育、研究,学习着手。非洲应该向中国学习传统医药如何促进现代医药发展。我相信中国有这样的气度,去帮助非洲。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只想垄断市场,不会发自内心地想要帮助我们。对于传统医药,我是有信心的,我相信未来很多病都能被传统医药治好。同样,南非人民也相信这点。”
“事实上非洲人都喜欢传统医药。在我小时候,大多数人跟我妈一样,用一些植物的叶子就能治疗疾病。如果我受伤了,就放在我的伤口,两天就好了。如果发烧了,放点什么喝了就好了。但是我们长大后学习医药知识,有了计量的概念,然后觉得自己的药不行了。怀疑自己的药品。说实话,我对此很不开心。
我个人还是非常传统的。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我研究中国茶叶的药用价值。我所研究的也就是在可变压力下茶叶的反应。事实上在古代中国,茶叶是种药。
“我们对待中国传统医药的态度是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中医这个东西,不过我们对它的了解渠道与西医有很大不同。人们更喜欢西医。我们没有途径去接触真正的传统中医药。有不少中国商人,会带一些什么草药过来,但效果不行。至于中国的官方人员,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讲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展望,不是实际问题。
我认为你们可以选择在非洲的某所大学建立一个学院。不是院系,而是专门的部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你们可以加入非洲当地的调研,进行学术合作,共建草药研究中心。但要记住,不仅仅是中草药,是传统医药,包括非洲的传统医药,要站在我们的体系上去推进。这个倡议南非的总统今年刚刚也提及过,建立一个传统医药研发中心。
但是,例如开普敦大学,是个西方化的大学。在开普敦,我们都是研究西药。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别人相信你们还是有点挑战的。我建议不要太直接地进入非洲,否则人们会排斥。我们自身是一直想发展非洲传统医药事业的。但我们缺钱,缺乏相关研究,缺乏相关的工业,但这正是中国的强项。但愿我们能建立双赢的合作关系。”
医疗援助组织在南非的情况
中国对南非的医疗援助由来已久。但是,Francisco却从未听说过中国医疗队。
“我从没注意到有来自中国的医疗队。在非洲我们偶尔会听说中国给了多少贷款,多少基金,但是人们还是不确定中国具体提供了什么帮助。一个是没有相关的宣传,另一个是因为我们对中国多少也有戒心。毕竟我们曾经被殖民过。如果中国跟欧美国家一样,也来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我们,那我们也不需要。
倒是我们会雇佣来自古巴的医生。有一些民间的NGO,他们干得很好。他们派遣自己的医生、团队,在研究传染病方面会有不少成就。然后他们会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他们的工作很有价值,我们一起在加纳做了抗击埃博拉病毒项目。
他们在当地也参与研究。我们一个研究疫苗的团队,就有跟这些组织合作。”
关于南非的传统文化
有传言说,南非人民觉得自己是欧洲人。在Francisco看来,南非的传统文化在面对很大的挑战。
“我们丧失了自己的身份。我们已经不再是非洲人了,只是保留了非洲人的外表。所有的东西都是西方的了。我们失去了一切,包括传统医药。我们试图摆脱西方文化,但是太难了。现在许多人都受西方影响,他们只关心发展。非洲人民会因为发展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身份认同就不会有发展。
这是几代人的自信。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中国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的创举。我发现中国人是勤于思考的。如果南非的团体联盟也能说,我们想要资本主义,但我们要有非洲的特点,那就太好了。
我们希望民主是有自己特色的。如果非盟能推动这点,我会过去祝贺他们,他们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了。不过,非盟是靠欧盟资助的,所以实现起来会很困难。我们没有机会制定自己的政策。他们会说那不行,你这样做我们不给钱。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百分之百由非洲出资的系统和结构。如果能实现,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主了,我们想要符合自身的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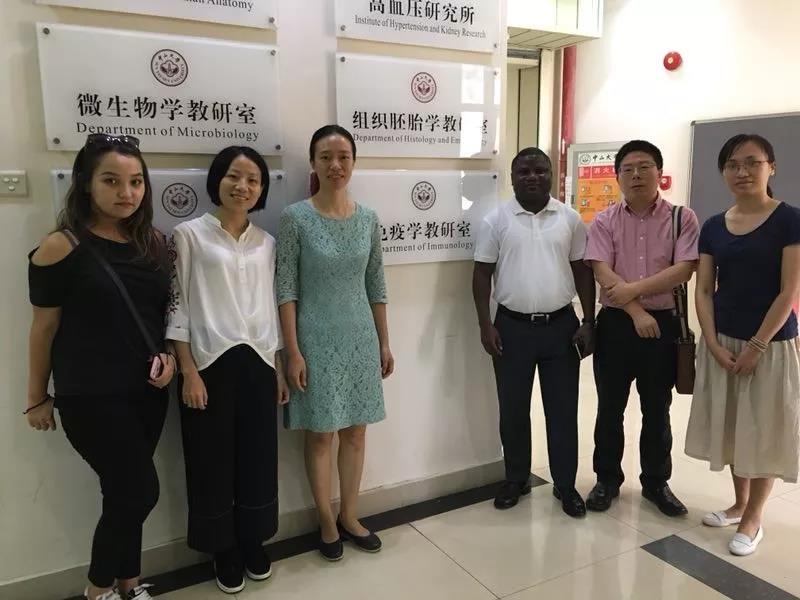
文图作者:曾驭然,陈家琪
注:该访谈得到陈功、吴晓瑛等人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同时,感谢参与访谈的董俊武教授,以及覃孝丽、迪达尔等各位同学。
文章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和看法。
神州学人杂志及神州学人网原创文章转载说明: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