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蟋蟀的鸣叫,是童年夏夜里最细微却最清晰的声音。对余光中而言,是40年后唤起乡愁的引子;对我而言,是16年前那个“留学生经典开局”的夜晚,在空荡屋子里听不懂语言却记住了寂静的声音。从那之后,我和“蟋蟀”一起穿越了四季与国界,不断成长,也在一次次搬迁与返航中寻找归属。
我的微信拍一拍是“拍了拍我梦里一去十六年的蟋蟀”,格式是两年前时隔许久再次来到美国时改的,灵感来源于余光中的《蟋蟀吟》——“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余光中40年后又听到了小时候四川的那声蟋蟀鸣叫,那时的我,距离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已有14年。
那是2008年,夏天。当整个北京都在为北京奥运会紧锣密鼓地准备的时候,我在奥运开始的前夕匆匆飞走了。幼儿园刚毕业的我懵懂无知,还处于“为什么我以后会见不到朋友了”的疑惑和无尽的晕机中,悄然到达了另外一片大陆。
父亲来俄亥俄州立大学做博后,我们一家三口便一起到达了这个极为陌生的地方。我也是头一次见识了“家徒四壁”的房子。在我的见证下,桌椅床柜等一切家具和生活用品一件件添置齐全。为了赶上奥运会的转播,电视是第一批出现的重要家电。听不懂语言,就像看连环画一样,看画面自行脑补故事。北京奥运会的圆满成功和中国金牌榜的辉煌成就还是通过亲戚朋友每天的电话传来的,那是我第一次真实地体会到割裂感——神州大地一片欢腾,我的周遭却静悄悄的。
不过这种割裂感没持续多久,或者说,还有更大的冲击等待着我,因为小学马上就要开学了。母亲是英语老师,尽管有她一个月的突击训练,但这毕竟是个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地方。艰苦就不必多说,我甚至要学两种教材——白天在学校里学8门课,晚上回家还有人教版的几本书等着我。父母对我用心良苦,我在成功融入环境掌握了英语的同时,中文和汉字也没有落下。除此之外,种族、文化、习惯等差异,歧视、抢劫、枪击等社会问题,也都是我在异国他乡必须要去面对的。小孩子的适应性强,再大的冲击和割裂感都能随着逐渐习惯轻松化解,苦尽而甘来。
孩童时取得的成就总让人津津乐道,因为那是一段最没有功利心的时光。在州科学博览会上做展演、出诗集、登报、给时任总统奥巴马写信、取得学校最高荣誉“校长奖”,孩子所看重的不是荣誉,而是做成了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有一件我一直极为乐意分享的小故事:应该是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学校里举办乘法比赛,感谢幼儿园时的“超前”教育以及父母的“家教夜校”,当时的我数学水平已然达到四则混合运算与分数,即将挺进几何变换,因此一路顺利进入决赛。一些常规问答过后,评委们发现我和另一位中国女生难以通过这种方式分出高下,于是决定以抢答定胜负。听到题目为7乘9后我脱口而出63,但我说的是中文的“63”,还没等我改口,另一位选手紧随其后说出“sixty three”,我落败。另一位选手还帮我解释,说我讲的是对的,评委老师们听到事情原委笑成一团,这可以称为我人生前10年里的最大趣事了。

后来我们又随着父亲回国,我在国内度过了初中与高中时光。大学时,我选择了一个中美合作项目。不是为了“重返”,更像是冥冥中的呼应——14年后,我又回来了。这一次来到的是新泽西,新泽西理工学院(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JIT)学校较小,中国学生也少,但却有着很强的凝聚力。从接机到迎新,我处处都能感到学联亲切的关怀。十几年前的记忆像是一块备用的拼图,此刻恰好补上。语言、文化都不再陌生,生活琐事也早已熟门熟路,我几乎是轻巧地落地生根。看着博士生学长学姐们每日分身乏术但依旧为学联忙碌,作为本科生自然义不容辞地加入,开始接手活动、赞助、宣传、海报等一众事宜。小事诸如烧烤、聚餐、团建,大事如中秋国庆晚会,我都可以独当一面,刚来不到两个月学联主席便开玩笑地说:“此事办妥以后必须擢升你为活动部准部长兼秘书部副部长。”
由于适应得很好,这个阶段反而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更加像是游刃有余的进取。我获得国际组织的青年经济学家奖提名,也作为副队长代表学校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名次。更是有幸,我确定了人生的下一站,一河之隔的纽约。


纽约的街道我并不陌生,本科时几乎每周都来,纽瓦克与曼哈顿只隔一河,坐地铁过去只要20分钟。生活没什么变化,但学业却有明显的变化。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和新泽西理工学院的课堂不同,我申请时还换了一个专业,从金融转到了环境,这是一个挑战,但我乐在其中。
有趣的是,“服务”好像成了我来纽约之后的主旋律。我住得离学校很近,刚入学那几周,朋友圈和新生群里总有人在求助:床塌了、门打不开、家具不会装……那些对新生活手足无措的夜晚,对我来说似曾相识。16年前,我和父母在空荡的房间里蜷缩着度过异乡的第一个夜晚;如今,我用自己的方式,为别人点亮那盏“第一夜的灯”。连着两周,我在周边各户间穿梭,装床、修椅子、开锁、刷墙,甚至是找黑中介维权。很忙,但也很快乐。
虽然搬来了纽约,但我与NJIT的联系始终紧密。作为mentor,我在学院的暑期研习项目中带着高中生做科研;学联有需要时,我也总会回来出一份力。除了大学的延续,那段来自高中的情谊也从未淡去——我在复旦附中海外基金会担任技术与活动部负责人,组织校友活动、维护校友会的联系。在异乡生活的这些年里,我逐渐明白,归属感并非源自一座城市,而是源于你为多少人留下了名字、为多少事点了一盏灯。
这一年我又有了个新的身份——私厨。由于我一直很喜欢做菜,又愿意投入时间去钻研,自认为做的还算不错。我常常摆上一桌宴席,招呼朋友来吃;也偶尔相应同学们的请求,做他们很怀念的东西。一位同学吃了我的鸡汤狮子头后感慨:“好想哭啊,真心感谢你,7月来了之后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好的菜品,不是工艺繁琐,不是味型复杂,而是能不能打动人心。
由于这个身份,让我遇到了一段奇妙的缘分。我家楼下有一家希腊餐厅,因为有学生特惠套餐,量大管饱,我几乎每日下课都去吃。一来二去和老板就越来越熟了。有一次聊天时提及我平时也会做菜,他很高兴,因为对于他来说,开餐厅只是为了生计,而做私厨可以让他尽情发挥创意,后来他开始邀请我去他组织的各种宴会。
我很珍惜这份友情,也喜欢他的菜品,于是将生日会订在了他的餐厅,却发现了一件更巧的事。他有一个弟弟,与他和他妻子的生日恰好相连,往前一周是他妻子的生日,向后一周是他的生日,但却遭遇不幸,在去年去世了。而恰好,我的生日与他弟弟的生日是同一天,他便说我的生日补上了这个空缺,让三个生日继续相连。从那以后,无论是在家宴上还是与朋友的聚会上他总对人说:“这是我弟弟。”而我,不仅多了个年长我近30岁的哥哥,也有了一个在美国的家庭。
后来我开始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帮他创建、运营餐厅账号,发一些餐品介绍和优惠信息,吸引了许多中国学生。餐厅生意越来越好,他开玩笑地任命我为“名誉经理”,从此,我不只是一位食客,更成为了这间小餐馆的一员。
有新奇温暖的缘分,也始终没有忘记那些陪我走过多年时光的老朋友。在NJIT时我有一位台湾室友,通过他,我结识了许多台湾朋友。我们不仅成为了每周都要相聚一次的好友,也逐渐在异国建立起一种特别的年味。每年过年我都会张罗一大桌菜,邀请他们与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吃个年夜饭。连着两年,我都有幸参加领事馆的新春活动,带着暖心包回家。暖心包现在也成为了我们每年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饭前贴福字与春联是我们共同的活动,饭后吃着小零食看春晚也是一份温馨与享受。
生活依旧热闹纷呈,学业上的探索也步步深入。因为研究逐渐成型,我开始受邀参加各类会议,从听众到展板展示,再到汇报发言。最近的一次,我有幸被邀请担任分会场主席。坐在主席台上,听着学者们侃侃而谈,低头再看看准备好的研讨问题,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我好像从教室,一步步悄然走到了台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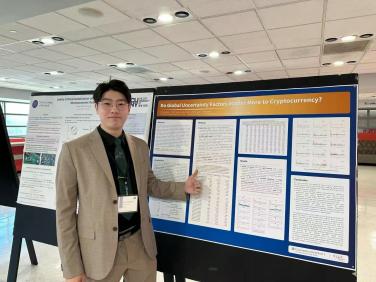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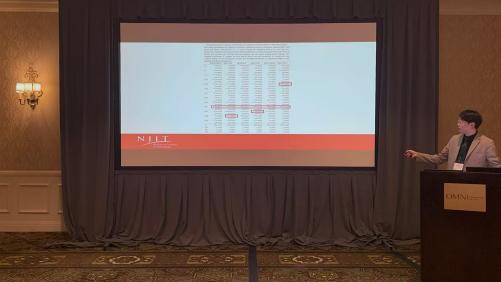
回过头来再看这16余年,我和余光中的心态似有相同,似有不同。余光中道:“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当他时隔40多年第一次回到故乡时感慨:“40多年过去,故乡变了。文化的乡愁是永远解不了。”乡愁是相同的,当举头望向上空的那轮明月的时候,我相信与之相伴的是玉兔与广寒,而不是古堡、蝙蝠和人变的狼。不同的是,余光中40多年不得而归,等到还乡时故土早已物是人非,大变了模样;而我随着21世纪的新中国一同成长,见证了祖国的巨变与腾飞,祖国也成为了我人生发展中的坚强后盾。近20年的求学路,也快接近尾声。去年,当我的一位好友毕业即将回国时,我写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赠予他。现在,也该轮到我回乡去建设祖国了。
文章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和看法。
神州学人杂志及神州学人网原创文章转载说明:如需转载,务必注明出处,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